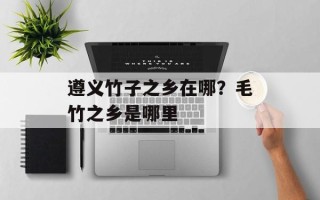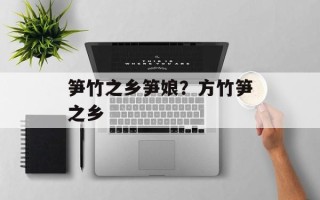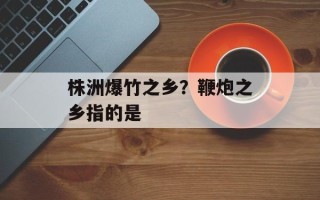其实闽北竹之乡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筇竹之乡,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闽北竹之乡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本文目录
一、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俗称闽北的城市是什么
南平市隶属福建省,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段东南侧,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俗称“闽北”。占福建省的五分之一,具有中国南方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特征。建瓯、武夷山、顺昌是“中国竹子之乡”,建瓯、建阳、政和是“中国锥栗之乡”,顺昌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杉木之乡”。
闽北境境内森林茂盛,雨量充沛,溪河纵横,水库棋布,水力资源相当丰富。境内的闽江和建溪、富屯溪干支流,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87.37万千瓦,居全省之一位。
1、东汉建安初分侯官北乡置南平县,属会稽南部都尉。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后属建安郡。西晋太康初改名延平县,仍属建安郡。南朝宋泰始四年(468年)废入建安县。
2、五代晋天福八年(943年)王闽以延平镇置镡州。开运二年(945年)地入南唐;次年州废,改置延平军。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升为剑州,六年置剑浦县为州治。宋为南剑州治。
3、元属南剑路;大德六年(1302年)复名南平县,属延平路。明、清属延平府。历为州、路、府治。1912年废府留县,1913年属北路道(次年改称建安道)。1 *** 8年直属福建省。
二、区域社会史视野中的闽北乡族社会
区域史是研究历史的一种 *** ,也是一种方 *** 。最近几十年,历史学以年鉴学派为旗帜,在与人类学、社会学不停地交叉碰撞和互融中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新史学、区域史、社会史,或称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 。这类新史学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关心整体的历史,或者说整体史的研究。其中,区域史明白宣示是通过“区域”对象,或问题的形成过程、机制与意义。
通过区域史的研究途径,在具体空间下逐步重建的历史面貌,应该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以前的历史社会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 *** 、大众运动和主要的文化变迁,他们寻求规律、趋势、类型和象征序列,企图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则,呈现出历史的可认知整体。然而,历史毕竟是复杂、多元、重叠的,区域史的研究不在于探求普遍规律,而是一种允许研究者加入“叙事”(narritive)风格和自我理解的“贴近式”研究,一种尽量贴近真实——但不可能完全真实的历史探求途径。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旨趣、研究设计和现实关怀都可能影响最终呈现的区域历史面貌。因此,与依赖抽离区域脉络 *** 而成的历史材料综合而成的“整体”历史相比较,区域史更具有特殊 *** 和独特 *** ,甚至可以得出不同的历史意义和结论。
区域史的研究既非历史学专属,也非人类学的创新,我们更好将其理解为一种方 *** ,它主要是由历史学与人类学在长期碰撞中互相“取长补短”而形成的,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区域”包括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地方”,区域史即是从地方的角度不意味着完全站在当地人的观看立场。克利福德?格尔茨仍坚持人类学家应有自己的解读,他倡导人类学应该“从我们自己对调查合作人正在做什么或我们认为他们正在做什么的解释开始,继而将之 *** 化”。由于人类学研究是跨文化研究,其对象是比较不可比较的文化,因此,承认地方 *** 知识体系和解释话语的自主 *** 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前提。同时,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的连续 *** ,他认为文化形态并非静止的形态,而是一个流动的活的过程,文化形态正是在行为之流中得到表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关注某一地方的具体事件,并将之纳入到地方与 ***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框架之中去分析,使这一偶然事件转变为具有普遍解释 *** ,超越地方 *** 意义的历史 *** “事件”,这也是区域史研究中的地方特色。
区域社会史的观察对象以传统社会为主,就中国的区域史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于对明清以来的传统社会的“区域”进行研究。在这样的前现代国家中,区域乃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分散于各地的村落组合而成的。“区域”与行政边界既交叉又重叠,形成了形形 *** 的区域:有的是以某一特定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形成的生产区或贸易区,有的是因某一河流而形成的流域,或者以某一特定山脉、地形走势、气候环境、族群居住地形成的区域等等。而不论何种区域,村落都是其最基本单位。作为一种“地方”的承载体,村落研究是区域史研究的基础。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社会学就开始运用“社区研究”大的有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大部分以村落为着眼点,试图通过对村落内部的日常生活方式、组织结构、 *** *** 、人际关系等因素的“深描”,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或本质特征。早期的村落研究,过于关注于村落内部的同时 *** 结构和组织,而忽略了村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尤其是宏大的 *** 经济背景对于一个村落的具体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学、人类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局限,开始从比较宏观的视野来研究中国乡村聚落。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威廉?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通过对四川成都平原的乡村集镇的研究,从区域市场体系的角度揭示了无数分散的乡村聚落是如何通过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这些层级市场体系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总之,人类学对中国乡村的村落研究,无论是针对单个村落的“社区研究”,还是区域视野下的“跨村落研究”,其关注的重点都在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这与区域史关注乡村社会生活本质的学术研究旨趣也是相合的。
对历史学者来说,研究民俗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民俗是一个表象 *** ,这个表象 *** 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历史结构。由于区域史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居住于乡村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和下层民众,而在传统中国,这些普通百姓并不识字,因而没有留下可读的历史文献。
面对这样的群体,民俗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普通民众传承历史和表达文化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各种民俗事项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另外,传统的史学研究用典籍解释典籍,但那些考证的、版本的、音韵的、训诂的小学功夫往往无法深人揭示典籍的意义,更无法让我们回到当时的情景中。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回到日常生活才能明白。
从区域史的角度来看,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 *** *** 、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时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大量乡规契约、地方文献、口述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在微观的地方史研究中,研究者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 *** 研究与结构 *** 分析、国家 *** 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眼光向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历史。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向来就有关注底层社会的传统。“贱民能开口说话吗?”或者说,能否通过对贱民经验的认知和表述,重新创造出精英文化?这一悖论被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反复探讨,并在学术界形成了通过书写贱民的历史和文化,来找寻到精英 *** 之外的历史的一种尝试。
作为一种研究趋势,微观史学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 *** 件。这种研究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区域史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了微观史学这种研究旨趣,注重对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关注,研究对象往往是极为具体的村落、家庭与个人的日常行为。
(三)对闽北地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在福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史上,闽北山区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明清以来,闽北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冲突的演变、家族组织的成长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和时代特征,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对福建和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40年代初他发表的尺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1944年版)两书,就是根据在永安乡发现的一批民间契约文书所做的关于闽北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傅衣凌强调应该从社会经济的层面分析佃农经济与抗租斗争。他大量使用当时学术界不很重视的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地方史料,对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问题进行论述,考察所谓的“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这些研究也为中国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其纂写的一系列 *** 中,特别是关于闽赣或闽浙赣毗邻山区社会经济史的 *** 中,曾就明清时代闽北山区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矛盾冲突等基本问题,提出过一些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之一,从长期来看,在山区的经济生 *** 系中,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占着主导地位,农业人口所占比重更高,但由于山区农业土地十分有限,加以土地占有较为集中,因此,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山区生活极为不易;第二,山区农村为应对人口压力和生计困难问题,消极的办法就是普遍地溺婴,较为积极的方式是从事其他生业,如从事土产的加工生产(如种竹制笋、造纸、种茶制茶、种香菇木耳等),或“懋迁货殖”,外出从事土特产的贩卖,于是在明清时代闭塞的内地山区,农业出现了多种经营,人口职业构成有了不少的变化,人口流动和物资流通开始活跃和频繁起来,这对于维持生计和自然经济的内部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在此基础上,山区商品的生产,山区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出现,闽浙赣省级商路的开辟,各地商品之间的流转与交换,构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成为明清时代闽北山区经济的新因素,这显示了山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是,由于山区远离市场,交通不便,更由于旧的社会因素,如乡族势力的干涉和封建土地 *** 的存在,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非常有限度,这又反映了山区社会经济迟滞的一面;第四,山区农村的乡族势力异常强大,这是或以祠堂,或以神庙,或以某种会社为中心联结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他们对田土、婚姻、商船出入、农业生产、生产技术、度量衡、贸易习惯、市场、运输权、财产外移、人口迁移等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的干涉,极大地阻碍或影响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第五,山区农村的土地占有和集中程度十分严重,有私人地主和乡族集团地主,私人地主中尤以数十亩左右的中小地主为多,而乡族地主的祀田、义田、祠田、族田、庙田、学田、茶田等同样居于重要地位,地权的集中造成佃农在农村人口构成中占很高的比例,也由此形成尖锐的主佃矛盾关系。
1980年以来,在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启发下,以厦门大学历史系及人类学系为主体的学者对闽北山区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杨国桢根据明清福建土地(包括山地)买卖契约文书,考察和分析了明清时期闽北山区的土地租赁、买卖、地权分割和“一田二主”制的形成等,认为山区土地的买卖与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反映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权的分化和乡族地主势力对土地和经营的把持、干涉,以及土地资本、 *** 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密切结合等因素又阻碍了山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因此,整个明清时期闽北山区经济的发展非常有限。郑振满则主要从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结构人手,运用大量族谱、契约、碑刻等民间文献,集中考察了明清以来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表现形式、基本结构、发展过程及历史成因,分析了闽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认为乡族经济主要包括
族产和地方公产两大类。由于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了强化,同时也阻碍了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正常发展,从而延缓了封建的土地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解体过程。
徐晓望依据方志、文集等资料的记载,从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山区商业 *** 农业的发展和山区乡村工业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明清时期闽浙赣边区山区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地位,认为明清时期包括闽北山区在内的南方山区经济是比较发达的,山区商品经济、商业 *** 农业和乡村工业都有相当规模,更重要的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来看,山区是工场手工业的摇篮。刘秀生则对清代闽浙赣山区的棚民经济做了研究,他认为在清代闽浙赣(包括闽北)的棚民经济中存在着雇佣劳动和货币地租,在沿海和山区之间出现了特征显著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经济,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方面起到了率先的作用。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上述对闽北山区经济的讨论大都难以脱离“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老套论题,但这些研究仍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明清以来的闽北地域经济与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和极具启发 *** 的假设。
区域社会史视野中的闽北乡族社会他认为造成闽江流域这种经济单向 *** 倾斜的最主要因素乃是这两个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闽北山区山多林深,交通不便,从而形成了较为传统保守的农业社区,闽南地区则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向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和地区拓展,形成了北方与南方、“居”与“游”的格局。在这多种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 *** 因素的作用下,闽江上游山区的农村社会进步缓慢。戴一峰集中考察了近代闽北山区的初级市场、商品生产与航运业,认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初级市场,尤其是茶、纸业等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初级市场,实质上是近代由外国侵略势力所 *** 纵的买办 *** 商业剥削网伸向山区的触角。 *** 者对小商品生产者的控制、盘剥,严重阻碍了闽北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自然、社会环境的险恶,又极大地牵制、阻碍了闽江航运的顺畅发展,使其步履蹒跚、进步有限,从而反过来又制约了闽北山区商品市场与外部市场的联系,以致闽北山区大量分散的、与市场信息隔绝的商品生产长期存在。
此外,厦门大学历史系与人类学系的一批硕、博士 *** 也很好地延续了这一学术传统,对近代闽北山区的社区发展与变迁进行了相关研究。现代史专业水海刚的博士 *** 《近代闽江流域经济与社会研究(1861~1937)》,指出了流域口岸一腹地关系中腹地经济(闽北山区)对口岸的影响,由此造成了闽江流域输出商品的结构变动——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销场的木材和纸张取代茶叶成为主要商品,使得流域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渐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厦门大学历史系还有一些硕士 *** 运用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 *** ,对闽北乡村社会进行了微观的区域史研究,且时间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
三、哪个城市以竹子闻名
以竹子闻名的城市有安吉、建瓯、宜丰、会同、桃江、广德等。
安吉为浙江省湖州市下辖县,位于长三角腹地。竹制品、转椅、茶叶、笋制品、农用机动车、建材等产品都有上规模生产,具有轻纺、造纸机械、食品、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等门类齐全,上规模的基础工业,出口产品多种,涌现多种省优、部优产品、一批国优产品。安吉物产丰富,品质优良,是著名的“中国竹乡”。
建瓯,福建省北部农业大市,省级生态市和省级园林城市,是福建省陆地面积更大、闽北人口最多的县级市,是一座1800多年建县史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市疆域总面积4233平方公里,素有“金瓯宝地”“绿色金库”“竹海粮仓”“酒城笋都”之称。
宜丰县位于江西省西部(赣西)北九岭山脉南麓。宜丰森林覆盖率71.9%,林地面积达到203.8万亩,竹林面积84万亩,活立竹蓄积量1.2亿株,居全国第三位,全省之一位,是中国竹子之乡。
会同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怀化地区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缘缓坡,雪峰山脉西南,以中山、低山、丘陵为主,境内群山叠翠,更高海拔1437.4m,一般海拔300至800m之间。盛产木竹,具有2000多年的楠竹栽培历史,以“广木之乡”盛名。全国100个商品竹基地县之一,是我国南方集体林区的重要竹子产区。
桃江县隶属于湖南省益阳市,地处湘中偏北、洞庭尾闾,因境内桃花江得名。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竹子之乡”,全县有竹林50多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的竹林,有32处。
广德县,隶属于安徽省宣城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苏浙皖三省八县(市)交界处。广德县是“中国竹子之乡”。
四、福建省的最北边是哪里
南平位于福建省北部,东接福建省城福州市和宁德市,地处武夷山脉北段东南侧,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结合部,是福建的“北大门”。为闽江的发源地,建溪、富屯溪、沙溪在南平城汇合始称闽江。幅员面积2.63万平方公南平市标——双剑化龙
里,是福建省面积更大的行政区域,辖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四市和顺昌、浦城、光泽、松溪、政和五县及延平区,总人口305万人。境内山峦起伏,河谷纵横,水系发达,属典型的中低山丘陵构造侵蚀地貌。是山水森林城市,闽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近代诗人郭沫若吟咏南平为“山围八面绿,水绕二 *** ”。南平市是福建重点产粮区,所辖10个县(市)有8个是全国、全省商品粮基地县,每年提供的商品粮占全省的1/3左右。近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又成为全省茶、果、食用菌、畜禽、淡水鱼、烤烟、油料等重要产区。南平市是我国南方主要林区之一,素有“绿色金库”之称。森林覆盖率达68.3%以上,木材总蓄积量1.15亿立方米,占全省的30%。同时,闽北又是全国毛竹主要产区,建瓯、顺昌是全国10大竹子之乡之一。随着水口电站和沙溪口电站的建成,闽北拥有了福建更大的库区。两个库区总水面达78.7平方千米,可开发水面67平方千米,成为福建淡水养殖的主产区。老南平
南平市不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而且自然风光优美、名胜古迹甚多。除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外,还有号称“华东屋脊”的东南之一峰,2158米高的黄岗山、九峰山、湛庐山、茫荡山、溪源庵、归宗岩、三千八百坎、熙春山、梦笔山、和平古镇等10多处省市级风景名胜区。南平风光奇秀,景色怡人,是旅游休闲度假理想之所。境内北有中国大 *** 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之一的武夷山,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生态景观交相辉映,以“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蜚声海内南平市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外,融国家级风景区、自然保护区于一体。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是“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角怪的故乡”,为 *** 带动植物“模式标本”的产地,号称“世界生物之窗”。南有三溪聚汇、环抱南平城的延平湖,是福建水口水电站的重点库区,库区水面达12万亩。全市有大小旅游景点150多处,其中国家级、省级以上景点占三分之一。南平因山川秀美、地势扼要,东达浙江、南连福州,西接三明,北出江西,自古以来就成为福建军事咽喉、交通重地。有“当水陆之会,扼八闽咽喉”之谓。唐末黄巢、宋末文天祥、明末郑成功都曾在南平驻扎举兵。南平市标“双剑化龙”,传说为上古名剑干将莫邪所化,矗立在建溪与西溪的汇合处,是福建母亲河闽江的起点坐标,南平的标志。“双剑化龙”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古时候,有两个妖怪分别在九峰山和玉屏山山上。有一个法师来南平地区游玩时。发现了它们,并用自己的双剑把她们都封印到了这里。所以也称“南平市标”。 2010年,福建省南平市申报的“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项目类别,序号2。

文章到此结束,如果本次分享的闽北竹之乡和筇竹之乡的问题解决了您的问题,那么我们由衷的感到高兴!